(本文根据2013年5月28日刘亮程先生在太阳成集团文字斋所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系列讲座“从家乡到故乡--文学的心灵家园与现实的身体居所”录音全文整理,并经讲座主讲人刘亮程先生与点评人王晓明教授校订)
从家乡到故乡
--文学的心灵家园与现实的身体居所
刘亮程
引 子
很荣幸能在太阳成集团跟大家探讨我所感兴趣的乡村问题。我来自新疆,今天刚飞了四个多小时的旅程,从一个远离海洋、少雨干燥的地方来到这样一个湿润的地方,身体暂时还有一点不适。新疆因为干燥少雨,所以什么东西长得都很慢,人们的生活也慢,我自己也是一个喜欢过慢生活的人。慢,它就是农业或者乡村社会的一种特征,跟其他的生活方式比起来,乡村社会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慢。因为伴随乡村的许多事物是慢的,农作物的生长是慢的,种子播下去,我们要等待种子发芽,等待幼苗成长起来,这个过程中,一株作物在慢慢生长,人得耐心地等下来,伴随着一颗作物去成长,一等就是几个月,大半年,一等就是一两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生活自然就变慢了,人的心态也就慢了。我理解的所谓乡村文化,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等待作物生长的缓慢的时间里,被人们一点点地熬出来的一种情怀、一种理念、一种对待生活或者过生活的方式,叫慢方式,我们快不了,因为比我们更慢的东西在拖延我们、在缠绊我们、在挽留我们,哪些牛呀,羊呀,植物呀,都让我们慢下来,我们快不了,这就是一种乡村生活的慢。我理解的慢,也是一种我们对待生活或者生活对待我们的方式,只有慢下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心境、才有时间、才有那样一种细心去对待生活,去看待生活。慢下来的时候,生活的细节才能被我们看到,我们才能够用心灵去感觉到某些东西,快的时候,我们是遗忘的。蚂蚁很快,我观察过蚂蚁,所有的蚂蚁都在忙忙碌碌,没有一只停下来,如果哪一只蚂蚁停下来了,那么它必定是快死了。我们人和蚂蚁的区别在于,我们很多时候也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不知疲惫,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停下来想事情。蚂蚁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干事情,我们有时间停下来想事情。想事情是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许多动物不会停下来想事情,我们会。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我们成了不一样的人。大家今天坐到这,也是停下来,跟随一个来自新疆的人一起想事情,我想这样一个交流也变成一个能够想事情的交流。十多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村庄》,在那本书里我塑造了一个叫刘二的闲人,没事可干。大家知道传统的中国文学塑造的都是勤劳的人, 在大地上起早摸黑、忙忙碌碌的人,操劳着脱贫致富的人。 我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塑造的刘二这个人,不关心大地上的春种秋收,不关心一年四季中的起早贪黑。他关心一朵云的事情,关心一朵花的事情,关心一场风的事情,关心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不关心的事情,我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写出了我个人对乡村的一种情怀,一种闲情怀,那一村庄忙忙碌碌的人终于养活出一个可以不用劳作,可以朝天上望的人,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抬起头来去想事情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一个人的村庄》塑造的一个成功的人物。许多评论家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很少关注到我所关注的这一点,“他”是一个闲人,这个闲人闲到什么程度,他从来不顶风走路。新疆多风,他到哪儿去都顺风走,刮东风的时候朝西走,东风停下来他停下来,反正闲人无事可做嘛,刮西风的时候再朝东回来,如果风不起的话,那就停下来,反正没事可干。他到谁家去也从不动手推门,等风把门刮开,进去后风又会把门关上。这个闲人还关心一件最大的事情,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一个人早早地站在村头迎接太阳初升。他认为此时此刻天地间最大的事情不是你家的麦子熟了,不是你家的牛羊下崽了,而是太阳升起了。太阳升起了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一个村庄没人关心,那么他想当然的担当起来关心这件事情。每天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一个人站在西边的沙包上,目送日落。他认为此时此刻天地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太阳落了。难道这不是最大的事情吗?难道还有比太阳落山更大的事情吗?没有。他要代表一村庄人目送太阳落地,然后他安然地回家去做他的梦。这就是《一个人的村庄》中这个闲人所做的事情。闲人不忙忙事,他是把大地上的事情放下,把春种秋收放下,把一村庄人的劳动放下,去单独地开始想事情,想劳动之外的事情,想天上的事情,想一场风的事情。就这样地空想,一个人在村里村外、天上天下的这样一种闲暇成就了这样一本书,叫《一个人的村庄》,就是一个人无边无际地虚想、胡思乱想,空想,他是闲想,它是一部闲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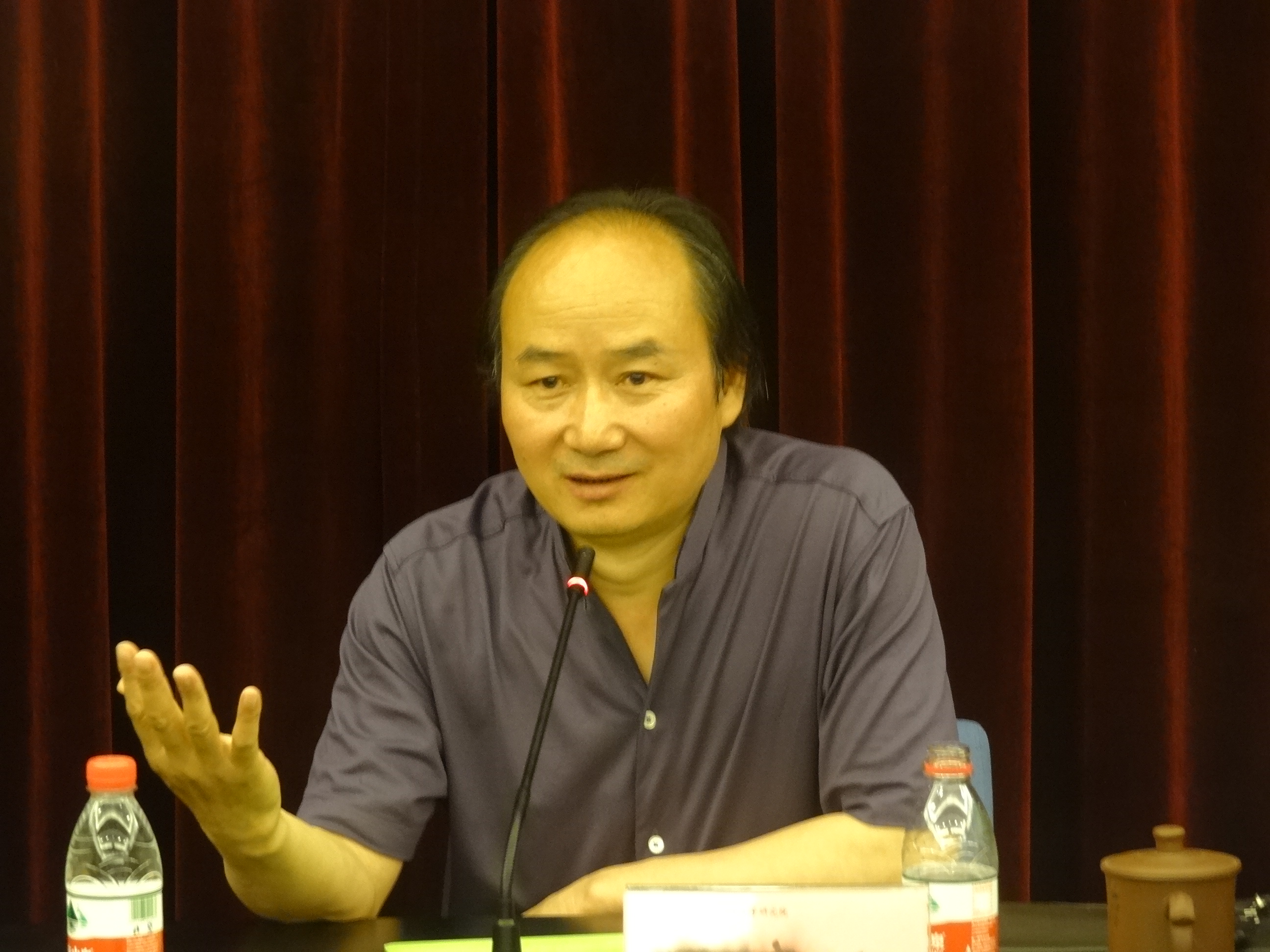
刘亮程先生
家乡和故乡 以上是今天的开场,接下来我要讲的主题是“从家乡到故乡”,它还有一个副标题,“文学的心灵家园和现实的身体居所”。我想通过我所理解的有关乡村、农村、家乡、故乡、乡土等概念来交流我心中的家乡和故乡。大家一般认为家乡跟故乡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是我个人的界定是,家乡是地理的,故乡是心灵和文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地上的家乡,和一个身体和心灵中的故乡。你出生的时候,世界把一个叫家乡的地方给了你,家乡用她的阳光雨露,用她的鸟鸣狗吠,用她的人声,用她所有的气息迎接了你。家乡似乎在你一睁开眼的时候就把整个世界给了你。家乡给了你许多没办法改变的东西,我们可能有时候并不觉得家乡给过我们什么,但是你仔细想想,家乡确实给了你一些一生都无法改变的东西,比如你的口音、味觉、看人看事物的眼光、走路的架势、说话和微笑的动作、你的表情、你以后处世的态度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就是你家乡给你的,并不是某个学校给你的。家乡在不知不觉中给你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知觉,你在浑然不知中领受了家乡给你的那样一份厚重的礼物,然后你带着这样一个包袱,去行走,去远离家乡,并不知道家乡馈赠过你什么。 许多作家都在写家乡,我也是一个用我所有的作品在写家乡的作家。我想作家写作跟平时生活一样,是需要有一个家乡的。为什么作家会从家乡出发, 会把他的代表作或者他认为最重要的作品,去放在抒写家乡上。这是因为当一个作家走入家乡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身份,他会在他的家乡,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在他的亲人中间,找到他自己的位置。我们在一个陌生地方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一回到家乡,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这是起码的一个家庭位置,我们会知道我在家乡中的一个辈分,当你找到自己的一个辈分的时候,整个家族体系其实就被你唤醒了。你是中间的一个环节,你是某某某的儿子,某某某是谁的儿子,往上推几代,再往下推几代,整个一个家庭链条就出现了。这时候你就明白自己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自己是连接祖宗和子孙的一个环节点。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连接点,连接祖先和子孙,当看到这个点的时候,一个作家就可以开始写作了,就可以去完整地叙述。 家乡还会让一个人变小,一个人无论在外面取得了什么成就,回到家乡他都是小的,是一个孩子,因为你的孩童记忆留在那里,还因为你的长辈在那里。孩子这个位置是一个作家一生所追求的。当作家把笔墨伸向家乡的时候其实他是想回到原点上,回到他初来人世时感知世界的那个节点。每个作家都想写出自己初来人世时感知到的那个世界的样子,我认为人类所有的艺术都是幼稚艺术,它不是告诉你成熟和深奥,它在告诉你幼稚,它永远想表述我们初来人世时对这个世界的陌生感,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成熟。对这个世界的成熟不需要文学告诉我们,作家想告诉我们,当生活一天天地变旧,当每天的太阳都陈旧之后,作家仍然会在每天的每一个细节之中看出生活之新,这种 “新 ”的最高境界就是我们初来人世时睁开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你想想,当你降生人世时睁开眼睛,怀着一种好奇、惊恐、陌生的感觉看人是什么样子?作家都想呈现这样一种 “新” 。世界如此之新,每天每时每刻,我都像降生之初那样,这是一个作家的最好感觉。作家把他的笔墨伸向家乡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找这样一种感觉,这样一种对人世的陌生的感觉。熟悉的感觉不需要我们作家去写,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熟悉的生活中,生活陈旧无比。但是作家能看出生活之 “新”,能把你不知道的 “新 ”告诉大家,能把皮肤的感觉、呼吸的感觉、把心灵的感觉告诉大家,这是文学的家乡医院。 那么故乡是什么呢?当这些家乡的所有情怀,所有生活融入到一个人的心灵的时候,故乡其实就变成我们心灵中一块硬东西,挥之不去的东西。家乡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小地方,我们通过这个小地方获得了对这个世界的完整的认识,对这个世界的完整的情怀,这些东西最后成为我们心灵的故乡。我界定的家乡是地理上的一个小地方,故乡是心灵中的一种永恒存在。一个远走他乡的人,内心怀揣这样一个不变的故乡,我们每个人都是怀揣一个心灵的故乡在他乡流浪,在他乡生活,过着一种非家乡的生活。 那么现在的城镇化建设,其实它做的一件事就是消灭家乡,把每个人的家乡都消灭干净,让我们不留存家乡记忆,让我们带着心灵中的故乡在一个陌生的街区生活。 当然我不反对城镇化,我也在城镇生活这么多年,乡村是我们人类的第一家园,城市是第二家园,我理解的乡村是一种适合心灵生活的家园,城市是一种适合身体生活的家园,我们城市的设计理念就是充分地愉悦人的身体,它整个体系是为人的身体服务的,让人生活其中,舒适无比。但城市不考虑人的灵魂。它所有的建构都是物质的。城市尽管也有寺院有教堂,但它最终的一个出口是火葬场,它不能像乡村那样,接纳人的生,然后接纳人的死,乡村有祖坟,当你的一生在乡村完成之后,你有一个很近的归属,叫祖坟,入土为安。城市没有这个。城市的火葬场最后让你的一生灰飞烟灭。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火葬场出口,它对生命有残酷的警示意义,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识之一。

王晓明教授
乡村和农村 那么讲完家乡和故乡,我再讲两个词,乡村和农村。我理解的乡村和农村跟家乡和故乡一样,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乡村是文化和精神的,农村是现实的。乡村是我们古人构建的一个精神文化家园,中国人的乡村自诗经、唐宋诗词、山水国画之后,就已经变成一个文化存在了,在现实的大地上已经不存在乡村了。乡村我认为是中国人的伊甸园,古代中国的“ 乡” 是一个自由的天地,大家都知道在古时,我们国家政权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广阔田野,是乡人自治、村人自治。也就是古代的乡村,是国家职权之外的一块自由天地,它是民间,权力之外的民间,大的国家事件不会从根本上触及到乡村这一级。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能如此悠久地传承五千年,就是因为我们有大片被称作民间的地方存在着,也就是国家职权之外的乡村这一块是相对稳定的。改朝换代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乡村这一级的安定,改朝换代是上层的事情,乡村这一级完整地保留着自己成体系的文化。 上个月我带着母亲到甘肃酒泉老家去了一趟,以前我认为乡村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被毁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我的老家的情况告诉我,这种文化在民间依然那么牢固地存在着。我的老家在甘肃酒泉金塔县的一个小村子里,那个村庄显然已经被规划过了,巷道整齐,房子一间挨一间。但是你进到每家房子,它都是个小四合院,进门是一个照壁,照壁对着是一个正堂,堂屋,正堂中供奉著祖宗的灵位。然后两厢分开,大人住哪边,小孩住哪边,非常规范的四合院体系,儒家文化还在非常严谨地管理着这个院子,一点都没乱。老人该住什么房子,小辈该住什么房子,都没有住错,这非常之好。老人住哪儿,老人住东边,那个房子的建制你看看房顶上的木梁就知道了,非常规范。我们四合院的盖法,或者是按照我们传统文化的建制,我们放房大梁的时候都要大头朝东,我们认为东边大,小头朝西,老人要住在房梁的大头所在的位置,住东边,然后依次往后排,是这样的顺序。你有了这样一个房屋建制,然后每个人都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该睡哪,整个它就有序了,小孩不会无缘无故睡到东边去,这样就犯忌了,这孩子从小就知道大小,知道大小他就知道规矩了,然后他就有所讲究了。非常完整,整个村庄都是这样。我们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又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城市化,那样一个偏僻地方的中国农村,儒家文化依然管理着家庭,依然保留着那么完整的四合院建制,你想一下我们这个文化的牢固性,多么顽强。 还有祖坟,我们去上坟,老人会带着你,那么多年没有回来,老人第一件事不是让你吃饭,是让你先到祖坟上去看看,我的叔叔带着我到祖坟上去,把祖先从太爷、爷爷,一个一个指给你,然后指到最后空的那个地方,说那是你的,那是给你留的。我听到这句话就突然觉得毛骨悚然,但是很快又觉得非常安稳,有这样一个地方多好啊,你来这么一趟你就知道你到时候去哪啦。 我的叔叔给我说,亮程,你从新疆来一趟很不容易,你下一趟来的时候我不在地里就在坟里,你能找到我。你看,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他知道每个人都是安稳的,知道去哪,那个祖坟就在自家的地中间,挨着庄稼,活干累了歇脚的时候在坟头边上铺个单子,把简单的饭食摆上,吃之前,给祖先敬上一份。生和死是粘着的,你觉得那样的死亡非常温暖,它不是离世,我们把死亡认为是离世,到老家你去看看,那哪叫离世呀,还在村子里面,哪都没去嘛,只不过从地上到地下了,一个很小的区别。村子里的老人也没有死亡的感觉,也不怕死,一般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会恐惧死亡,但我到老家跟老人在一块谈的时候,死亡就是他嘴边的一句话,谈笑之间,仿佛一生就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因为他知道去哪儿,我们不知道去哪,我们只知道要去火葬场。 这是乡村,乡村是被我们的古典文学以及山水国画塑造出来的一块自然家园,唐宋诗词之后中国的乡村就不存在了,乡村变成一种精神和文化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存在于我们的情怀中,现在中国大地上所剩的只有农村,农村是农民生活的地方,是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劳作的地方。我们经常是怀揣一颗乡村之心到农村去寻找,结果找不到,因为乡村根本就不存在了,乡村变成一种理想,变成一种精神和文化了,我们一次次开车下去,穿过乡间小道,最后找到的是一片生长庄稼的破败不堪的住着贫穷的农民的农村。我们所说的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不是乡村问题,乡村问题是文化问题,农村问题才是现实问题。自古以来我们所谓的天下大乱,那肯定是乱到农村了,连农民都乱了,古代统治者最怕的是农民乱,因为农民手里有工具,铁锨、锄头,叉、镰刀,在冷兵器时代全是兵器,劳作的时候是农具,一旦乱起来全是武器。我们新疆有一种农具叫坎土曼,跟锄头一样朝下挖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砍头曼。所谓天下大治也无非是耕者有其田,农民温饱解决了。 我是一年四季都在新疆的南北疆农村中做调研,在看自己熟悉的农村一点点地在变化,旧的东西在消失,新的东西在出现,这个世界在变得越来越陌生。我以前在一片文章中写道:我对乡村土地太熟悉,即使我离开这个世间五百年以后再回来,我都能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乡村世界,因为我知道那条弯曲的路通向哪里,我知道田野上长着麦子、苞谷这些我认识的食物,每年五月的时候我会闻着沙枣花香找到我的家。 现在看来这危险,也可能我二十年之后回来,我就找不到家了。田野上长的都是我不认识的植物,我可能就不敢吃,不知道哪些东西是可吃的,哪些东西是不可吃的。现在的种植技术让好多我小时候熟悉的爱吃的东西消失了,变得怪模怪样,个头很大,现在的植物,一吃就不像人吃的东西,不知道谁发明的这样一种东西,高产量,但是没有人间的味道,它把人间的味道给弄丢了。 这就是农村。乡村作为一种文化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中,农村依然是那么现实的,那么沉重的存在于我们身边,没办法回避,也不能回避。新农村建设之初,我也提过一些建议,我提到农村应当怎么规划,应该保留哪些东西,但都没用。 现在的新农村住宅的一大特征就是,它所有的建筑里面没有精神空间,就像我刚才提到那样,我们老家的那几间破房子它都回腾出一间供奉祖先,但是现在的新农村建设,不管是盖十间房还是八间房,全是盛放物质,没有一间留给祖宗,没有一间留给我们的精神,房子很大很多都是盛放物质的,新农村设计者考虑的全是电冰箱放哪,洗衣机放哪,电视放哪,电脑放哪,放到最后没谁想起来把祖宗放哪,盖房子时也不会想到有一个正堂,正堂变成客厅,客厅中也没有一个安放祖先的位置,这是新农村的一大特征:把祖宗和精神丢了。 第二个特征,把人和动物分开了,也没给动物留空间。我们新农村建设是拒绝动物的,我们认为跟动物一起生活会得许多传染病,所以我们建筑的原则就是房和圈分开。我们以前的生活里房和圈是不分的,人的住房和牲口圈是挨着的,有一种邻居的感觉,有时候牲口走错了还能窜到人家里面去。它把我们延续了千年的跟动物一起生活的模式打破了,让人变成了孤独者,除了人还是人。在乡村生活中,乡民的心境是从人和万物中活出的一种理念,人的情怀兼顾万物情怀,人会在他的生活中考虑一只鸡的感受,他会为一只鸡、一匹马去做事情。他有空间,人和人不像城市那样近,在乡村,人和人之间隔着几棵数、两头猪、一只羊、几只鸡,他有一个缓冲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紧张是因为那些动物在调节,那些植物在调节,那一菜园菜在调节。邻里之间,有一排树,你别看这一排树,它是有缓冲的。但城市没有这样的空间,新农村建设把动物排除出去以后,它其实是让农民变成了只跟人打交道的城市人。 新农村和城镇化最终的目的可能是消灭家乡、消灭农民,让农民变成街区的市民。有专家预测,即使是非洲最偏僻的地方,五十年之后,城镇化也会全部实现。因为所有的资源和服务体系都会集中在城镇,你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岛屿上,怎么生活?这样的推论不知道是谁做出来的。千百年来,没有这样的服务体系,他们又是怎么生活的? 当然,城镇化是一个没法回避,谁也没法阻止的进程,我们只是在这样一个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踩一脚刹车,让它停顿一下,稍微慢一慢,想一想,这样一个在农业文明,或者说农村文化中生活多年的群体,这样一个巨大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当我们把他由农民变成市民的时候,当我们从他的生活中取掉那些菜地、羊肠小路、麦田和那些牛羊的时候,当我们把他从离土很近的温馨家园搬迁到高层楼阁上的时候,我们还应该给他们什么?我们不能把那么多东西从他的生活中删除掉以后,就给他一个空空的高楼,给他一个几十平米的冰冷的空间。这样的空间能让他们生活吗?他们怎么去生活?他们是人,他们内心的那种乡土情感怎么去延续。 我们让那么多的农民住在我们所提供的街区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能力把那些乡村文化、让他们安心生活的那些东西还原给他们,让他们这个陌生的街区怀揣自己所熟悉的乡土文化,或者乡村精神去生活,他们靠什么东西去生活? 乡土精神 再讲一个词,乡土,或者说乡土精神。我是一个写散文的人,写散文的人就是有一搭没一搭,东拉西扯,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地。我的演讲也是散漫的。 乡土精神是维系乡村文化的最主要的东西,我们一般认为,农耕民族没有宗教,但是我认为,乡土就是中国农耕民族的宗教。乡土一词蕴含两个概念,乡,是一个空间概念,表示四方乡里;土,是一个时间概念,表示生前死后。我们汉语中很多词汇都是空间和时间并构组成,乡土也是这样一个融合了空间和时间概念的词汇,有空间有时间,有现世有来生,我们生于土上,葬于土下,两种生活在乡土一词中完整地呈现出来。我们的乡土文化,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土上和土下、今生和来世、祖先和我以及后辈这样一个体系中完整成型,代代延续。中国人有一句讲得非常好的话,叫“人不亲,土亲”,这句话就是我们乡土文化最集中的表现,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的时候,可以不亲,可以有仇恨,可以有恩怨,可以有纷争,但是没关系,一代人一过,大地重新刷新一遍,当我们重新回到土下的时候,我们又亲了,在一把黄土中,我们能找到共同的祖先,在那里,我们没有仇恨,我们全变成土,变成一块泥巴,在土中,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终极,我们最后的归属,最后的安慰。这就是宗教呀,能够解决人的今生和来世,这不是宗教是什么?我们以土为尊的乡土宗教,如此厚重的乡土之土,承载一切,包容一切,生长一切,毁灭一切,这就是乡土。我们建立起所有东西,最后复归于土,然后土地又重新生长出万物,生长出我们的子孙。这就是乡土,我理解的乡土。 “乡村文化人士” 谈到乡村文化,我再讲一个前段时间我提出的“乡村文化人士”这样一个提法,以对称“城市知识分子”。大家都知道,城市知识分子是国家培养的,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教授,大家都是国家培养的城市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我称之为“乡村文化人士”,他们不是国家培养的,他们是自学的,靠家族传承的,靠乡土气息培养的。我们到每个村庄去,都会发现,那个村里面有一个人,他什么都懂,他懂得接生和接生礼,懂得生老病死,从生到死这期间的所有礼仪,他全懂,你家出现什么事,找到这个人,他就全解决了。你要结婚了,结婚有什么礼仪,说媒时应该怎么去操作,最后当你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家人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就叫乡村文化人士,他们懂得乡村所有的的礼仪,从生到死,他们全都知道,他们偶尔还会看病,偶尔还会算命,偶尔还懂点巫术。你的头疼了他会点几张纸燎一下,然后头就不疼了。有时候你经常夜里梦见鬼,他会带你去捉鬼,把鬼捉出来让你看,你一看,啊,鬼在这儿,然后你就再也梦不到鬼了。这样的人,每个村子都有,但是不多,一个村就一两个。假如一个村庄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去世,整个村庄的文化体系就断绝了。所以我曾经有过一个提议,国家给这些乡村文化人士发工资,让他们享受城市知识分子一样的待遇,给他们评职称。他们是国家没有投一分钱,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把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代代传承下来的人,他们是乡村文化的“活宝”。乡村文化是靠他们传承的,一个村庄少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结婚时第一道程序该干什么,到最后人生终结的时候,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只有进城了。 我们的乡村文化千百年来就是靠这些人在一代一代传承着,老人做的时候孩子在看,长者做的时候年轻人在看,我们在村里,做一个家的老大,你是要懂这些东西的,老年人做的时候,你是要看着的,因为你也会有孩子,孩子结婚的时候,你要知道婚礼该怎样操办——假如一个父亲都不知道婚礼该怎么操办,不知道该怎么嫁女儿,这也有问题了。等到你的老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为他送终,该怎样安葬他,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家里面的长子,必须要学会的,必须要懂的。你不懂的可以去问,村里面有啥都懂的人,你不知道的可以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一个村庄的文化,有这几个人就可靠了,其他人就可以放心了,不用操心这么多事情,去春种秋收就可以了。这些礼俗类的东西就让乡村文化人士去担当。我曾经建议国家按照教授级待遇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代代传承,让他们尽这些义务的时候也有些责任感。 但其实这很难。我们到许多村庄去都找不到这样的老人。这个老人一消失,这个村庄人就有好多东西不知道了,问那些年轻人,啥都不知道,等他们长老以后,他们仍然啥也不知道,然后一个村庄这种文化体系,就失传了。 当然,以后我们进到城市以,进入某个街区,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样的文化了。但真的不需要了吗?我认为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还有生老病死,我们还要过和我们祖先一样的日子,不管我们在哪儿生活,我们都逃脱不了我们的祖先、父母、爷爷奶奶所经历的那些人生阶段。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能安慰人的今生和来世的完整的体系,没有这样一种文化安慰,那么,我们去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还有一种其他的文化可以去安慰我们的精神吗? 当然,城市也会在它发展中不断地去有一些适合于城市人的文化和精神,比如教堂、寺院和其他等等。但是,毕竟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要把那么多农民迁到城里来过生活,把那么多农民要赶上楼去过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否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给他什么样一种心灵生活?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全部没收了,我们要让这些农民带着乡村文化、乡村精神进城,当然,这也不合适,这是城市管理所不希望的。 故 乡 最后一个问题,讲故乡。我是一个作家,我认为文学写作,就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过程。正如许多作家都在写家乡一样,许多作家从家乡出发,用他的一字一句,呈现他的家乡事物,他最终的愿望是,通过自己的书写,让一己的故乡变成许多人的家乡,变成人类的精神家园。我想这是所有的作家所追求的。 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写家乡,写到最后,他的家乡依然是那个小村庄,依然没有被很多人接受。只能说,那样的写作不具有故乡意义,只是从家乡到家乡的写作。优秀的文学都有故乡意义,就像我们在大地上生活一样,我们把一个小村庄生活成故乡的时候,家乡就进入了我们内心,文学写作也是一样的。我们欣赏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其实都是在找到一种作者所营造的,或者说作者替我们保留的这样一块精神故乡。我们从文字中找到了安慰,找到了兴奋,找到了激动,找到了悲哀,都是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文学都在塑造故乡。 我们说新闻在考证这个世界之变,没有变,没有新闻,那么文学在做什么?文学在考证人心之变,历代的文学家都在考证人心,当我们这个世界经历了千千万万的变化之后,经历了世世代代的动荡之后,人的内心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文学和文学家所考证的。我们的文学从古到今都在考证人心之变,那它考证出了哪些人心之变呢?人心到底变了没有?没有。这是文学告诉我们的。文学一直在考证人心之变,一直在追问人心之变,但是它一直又在维护一个最不可动摇的人心之不变。我们通过读诗经会发现,人类千百年来的爱和对自然的欣赏,没有变;读《荷马史诗》,读东方西方的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人类千百年来的战争、仇杀以及化解战争和恩怨的这样一种情怀没有变;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们会知道大地上的劳作和劳作的辛勤,千百年来没有变。那么现代人和古代人有什么区别呢?除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变了,我们的外观变了,我们的穿着变了,甚至语言都变了,但是我们内心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变。我把内心中不变的那一点东西称之为——精神的故乡。所有的文学,优秀的文学,都在塑造这样一块不变的,我称之为故乡的东西。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晓明: 感谢亮程精彩的演讲。我们重庆城市化剧烈程度在整个中国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而且现在整个中国城镇化的潮水是越来越大。这件事情在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也在改变中国大部分地方的地貌。人的生活一旦改变,地貌一旦改变,大部分改变是不可逆转的。即使以后我们知道搞错了,也回不来。当这样一个大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卷入其中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最多的声音,还不是来自城市知识分子,而是城市专业人士,他们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比如上海,把一个大的很有名的书店从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赶走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城市专业人士出来说,你看,这个地方,它走了以后,怎样应该把这个地方的土地收益最大化。这样做了以后,钱肯定可以增加多少,GDP可以增加多少。这都是城市专业人士在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样的变化。但今天,当亮程先生在讲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作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希望能更多地听到这样的来自文学的声音,这可以让我们重新反思很多习以为常的想法。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以前我们到一个农村,看到村里人对城市里的政治事情,谁上台谁下台,糊里糊涂,不大知道的样子,我们会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闭塞!听了亮程的演讲以后,我忽然觉得,其实应该庆幸,当城市里这些过眼烟云的事情忽而起来忽而消失的时候,辛亏中国还有很多地方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不知道,他还能延续自己的生活;因为不知道,中国大地上许多事情还能延续下去,没有被这些所谓上面的事情一搞,都跟着转——大地很稳定。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刚才亮程讲到的——故乡。我想啊,城市的故乡是在乡村,乡村是城市的根基所在。为什么大家都要到城里来?第一是城里赚钱机会多,第二,对有些人来说,城市是一个掌握权力比较容易的地方,因为权力集中在城市。可是,如果城市给人的吸引力只是钱和权力,那么所有到城里来的人,对城市是没有感情的,他要的只是钱和权,那一天城市不能提供给他权力跟金钱了,他就会毫不犹豫转身离开城市,城市跟他只是利益交换的关系,他不会爱这个城市,可是,还是有很多人真心喜欢城市,他不只是觉得城里钱多,可以掌权,他更觉得城市有很多别的好东西。其中最好的是什么?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觉得最好的,是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乡村所没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可是,城市的丰富性从哪里来?之所以城市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因为有无数不同的人从各地到城里来。而这种不一样,这种人跟人的差异,主要不是城市自己生产出来的。基本上城市只是一个收集者,一个吸纳和收集的地方。城外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外的生活,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无锡人跟常州人不一样,合川人跟惠州人不一样,每一个小城市的背后,都是一大片乡村,是这样的乡村造就了每一个小城市的不一样,这些小城市的人进入大城市,就把这些不一样带进了大城市,这才成就了城市的丰富和多样性。如果城市像今天这样扩展,把以前的乡村搞成工业化的农业地区,乡村人要么进城,要么变成农业工人,生活方式也一样城市化,那结果,就一定是城里城外大家都越来越相像。长此以往,城市还怎么可能有目前这样的多样性?光靠城市自己,能保持和发展这样的多样性吗? 所以,目前这种城市化要吞没一切毁灭乡村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是在砍自己的脚,把城市最吸引人的多样性的根砍掉了。 (录音整理:杨里娟)